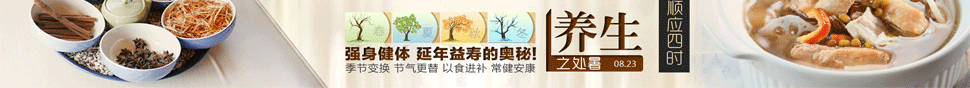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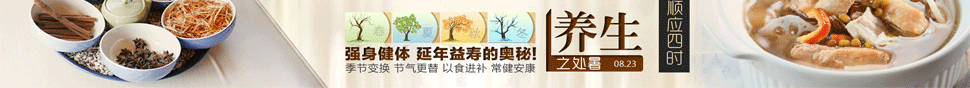
公元十世纪越南脱离中国获得独立后,与南邻占婆长期征战,越占对抗和越南征服占婆持续了近千年时间。越南在对抗中逐渐占据优势,边界不断南拓,十九世纪前期终将占婆完全征服。在越南政治和文化史中,“南进”一直是主题。
越南“南进”过程中,并没有将占婆人赶尽杀绝,而是将大部分占婆人同化为越南人。在“征占”过程中,存在一个吸收和转化占婆文化的文化融合过程。本章试图通过探讨越占交战中的文化交流,进而分析越南文化中的占婆因素。
一、古代越南与占婆文化的“近亲性”众所周知,越南深受中国文化的浸染与熏陶。早在漫长的郡县时代,中国封建统治者就大力灌输汉文化,越南自立之后,其统治阶级接受了中国的典章制度、使用汉字和读四书五经,越南深受中国汉文化的影响。而占婆自立国之始就是一个开放的国家,马印度进行商业交换,并且吸收印度的宗教、政治、法律和风俗文化。占婆使用印度文字雕刻碑文以记录宗教和政治法令。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越、占之间是完全不同两个世界的代表,双方的关系史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斗争史。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汉文化的影响多是局限于越人上层,而对生活在封闭公社中的广大越人影响较小,他们仍保存了民族的基本特色,如高脚屋、嚼槟榔、妇女地位高等。同样,印度文化对占婆的影响也应该适度看待。印度文化对占婆的影响尽管可能很大,然而,如果从其对当地社会的实质性影响而言仅仅是一道“薄薄的玻璃”,在这层玻璃下面,古老的当地文化的主要形式继续存在。
占婆并非是印度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其统治者有意地借鉴了印度的思想、艺术风格和组织模式。例如,早期占婆人对梵文的使用,不规范的表达方式和语法错误交织,这并非是因为占婆人对印度文化只有肤浅的理解或是占婆人能力的不足,而是出于将印度宗教文化与本体信仰融合的需要。所以,就两国地理位置和文化影响的紧密程度而言,越南与占婆存在某种文化上的“近亲性”。
越、占两国政治斗争中失败的统治阶层人物以及国内反对派人物,各皆向对方亡命投靠,并都企图借重对方的力量以回国重掌政权,这一政治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两国文化的“近亲性”越南与占婆的第一次战争即因此而起,年,越南驸马吴日庆逃奔占城,并因占城舟师攻打华间城。98年,黎桓征占时,管甲刘继宗遁巨占城,并窃据王位,后被黎桓派人暗杀。“公元年,占城田子地婆刺、乐舜、乍兜、罗继、阿挞刺五人来投奔越南。
占婆统治阶层投奔越南是很常见的事,由此才使得占城国主借投降之机,而能劫掠而回,陈裕宗时期,占婆制某投奔越南。制某是占婆先主制阿难的儿子,先王死后,制某与制阿难的女婿茶和布底争夺王位,后制某败逃越南并引越军大举攻伐占婆。杨日礼之乱后,日礼的母亲出亡占婆,后引占军寇掠边境。
年,占城主制篷我战死后,其部属罗皑引余众归至占城,据国自立。前王制蓬我的儿子制麻奴迤难与制山罕害怕别杀,逃亡越南。制蓬我多次入侵越南,三次攻陷升龙城,然而越南仍接纳了他的儿子,井“封麻奴迤难为校正侯,山条为亚侯”。公元年,又有占城管象头目类、要二人来降。这么多起的双向亡命现象,足可看出越南和占婆文化上的“近亲性”基础以及双方相互间政策上的某种“宽容性”。
衬托出越、占间文化的“亲近性”的,还有另外的插曲。譬如,陈太宗的一个儿子昭文大王陈日炳,爱好橘外国人做游,他竞乘坐大象去到了一一个占人聚居的村庄(安置李圣宗远征时俘回的占城人的村子),他在那儿住了三、四天才回来。°叹年,曾向军民发布禁令:“禁穿“北人’冠服及仿说‘占、牢语言””。这就反映出了在越南社会上,穿用中国服装及讲说占城话、哀牢话并非罕见之事。
二、战争对越占文化交流的促进马克思在论述古代战争与历史演进的关系时曾指出,“战争本身是一种通常的交往形式”。战争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沟通。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除了商道路,就是战道。“文明早期,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不同语言的种族之间,战争是实现其文化融合、血缘融合的方便快捷、高效率的方式,尽管是残酷的方式”。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评价历史上的些战争时指山,“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古典希腊文化普及到整个中东,形成一个新的文明: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具有深远的意义,还因为他们促进了欧亚大陆内那种相互得益的交流: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起了使欧亚大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紧密地融合为一体的作用”。越南与占婆五百余年的争战,促进了两国交通的发展,大量居民和俘虏被迫迁移,从而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
(一)越南伐占促进越占两国交通发展交通是战争的一个基本要素。在越南征占的历次巨大胜利中,越南一方必然做了充足的准备,除了训练士兵、修造战船、广积粮草,还保证的海陆道路的畅通。“海道新港成,帝征占时,厉铜鼓山,至婆和江,山路险难,人马困惫,又难往来,乃使人开港。至是成,舟楫所至,皆得其便”。"此条记载的是年,黎桓讨伐占城时的情况。
铜鼓山在马江上,位于清化省安定县境内,而婆和江则在清化省静嘉县南部。从铜鼓山到婆和江山路险阻,而海路波涛汹涌又难往来黎桓就命人开凿渠道,走江道至婆和江,而后才沿铁渠进入义安,再从此沿海道进入占城。公元年,黎桓又“命辅国吴子安率三万人开陆路,自南界至地哩”国。当时,越南的南部边界是在横山,地哩位于广平省。
春宗用黎季犛言,督清化、义安和新平的人民修治从九真直到河华的道路。当时的九真州是清化省的南部,修治九真到河华的道路,为了可以从陆路由清化行军到横山,为了能够与常常干涸的水道并行。黎季答受命督义安到新平、顺华的漕运。
胡朝仅存六年,其对占城取得突破性进展,道路无阳是其取胜的因素之一。公元年,“汉苍修治道路,自西都城至化州。沿途置庙舍传书,谓之千里衢”。年,“汉苍开莲港,自新平至顺华界,泥沙喷起,用功不成”:“化州腰海门决,汉苍命以京军填塞之”。胡朝曾把我国领土扩展到广义地区,并增设了升华路。为了加强统一,胡朝又设置了从升龙北至谅山、南至升华的驿站。
公元年,黎仁宗命黎受领兵十万征占城,“黎受等诸君至占城離江、多郎、古垒等处,开通水路,筑立城堡,与贼相战,打破之,乘胜直抵户耐海口”。越南至占婆有三种道路选择:山道、海道、海陆路。早在11年,陈英宗征占城时,“至临平府,分军为三道。惠武王国填由山道,仁惠王庆余由海道,帝亲率六军由陆道。陆并进...°至黎圣宗征占时,海陆交通日趋完备。
《征占日程》一书详细记录了圣宗征占时期南行路程,包括陆路、水道行船和海道巨艘,以及途径海岸著名海港、海口历史传说与事迹和陆路所经地区著名营寨、沿海战略地区和占城国境的重要地形略述。根据征占日程,其大致路线是,自升龙出发,二十日到横山脚下,二十一日到灵江岸边。三十三日到海云山,六十日进入占城国境。
国越南与占婆之间的交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不但基本满足了战争的需要,而且也加速了两国文化的交流。交通是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有交通的地方才会出现人群,正是水路交通的便利有效的促进了经济贸易往来和移民迁徙。升龙至升华地区沿线驿站的建立,为两国使节往来提供了基础条件,又进一步加强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二)被动性移民越占两国居民的相互迁徙,只有一小部分是寻求政治避难的主动性移民,如李太宗时期,“占城国守布政寨人布令、布哥、蘭沱星,率其部属百余人来附”;又有仁宗时期,“占城国人波司蒲陀羅等三十人来附”。多是这样几百人或者几十人的规模。而战争则引发了大规模的被动性移民。
被动性移民或者称之为强迫移民,主要有两种途径,其是战败的俘虏,被强制带到异国。人口是占婆对外掠夺的主要目标之一,并且已经详细列举了占婆进行的这类侵略,此处不再赘述。可能大虽被俘人口被当作奴隶出售其它国家,但其中必然有一部人留居占婆本国。同样,人口也是越南历次征占的重要战利品。前黎朝第一一次征占,即“俘获士卒不可胜计”。
李太宗征占之役,“帝还自占城,告捷于太祖庙毕,御天安殿,涉饮至礼。是日,群臣献俘五千余口,及金银珠宝之物品。诏俘虏各认部属,居之永康镇,直至登州(今日化是)置乡邑,仿占城旧号”。此次战争,越军胜利,直捣占婆都城,所俘占人被分配于边远的永庆州和登州,以开垦荒地。越南皇帝还掳掠了已故占婆国王的好子,年,皇帝在升龙城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宫殿来安置占婆女脊。李圣宗征占时,又俘获五万余人,班师还朝后,献俘于太庙。
年,黎圣宗进兵围困闲盤城,“俘获三万余人,斩首四万余级”。被迫移民的第二种途径是,越南统治者迁徙本国居民去开发新从占婆获得的领土。对于越南南部历代边界的变迁,我们早已熟知。李朝时期得地哩、麻令、步政三州。陈朝时期,得鸟、里二州:胡朝时期,越南又吞并了占婆的占洞、古垒二地。为了发展和巩固新的领土,越南朝廷都会迁入北方的居民。原来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占婆人,部分逃回本国,但更多的居民留在原地。胡汉苍曾封占城投降过来的效正侯制摩奴迤难为古垒县上侯,镇瘦思、义州,以招抚属占群众。
结言从横山至虬蒙这片广大的地区,新迁入的居民与从前在这里谋生的老乔民一起开垦土地,京族人与占族人杂居。公元年,黎圣宗谕广南参政范播宗说:“广南乘政司军民生男十五岁以上,俊秀好学,至乡试日,其本处乘宪二司共同选取,具本充本府生徒”。这说明,当时占城人已与越人密切同化了。随着越南和占婆人口的相互迁入迁出,两国人民对不同的文化习俗相互磨合、接纳和学习彼此不同的文化传统,极大的带动了越占两国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